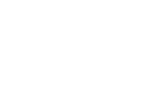民航局公安局“六严”工作办公室政策研究小组
【摘要】善治必然是多种治理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规范层面,国家制定法是核心的治理模式,与此同时,基于治理机能上的一致性,公共政策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空防工作领域,公共政策也因其更强的适应性、更为灵活的调整方式和更为多样的实现机制,形成了其独特的治理优势,并作为一种导向和调配机制,具体的参与到民航安全保卫工作中。
【关键词】空防;公共政策;社会治理
英国学者R·科恩(Morris Cohen)指出:“生活需要法律具有两种相矛盾的本质,即稳定性或确定性和灵活性。需要前者,以使人的事业不致被疑虑和不稳定所损害;需要后者,以免生活受过去的束缚。”[1]在国家制定的法律之外,空防公共政策作为一种规范形式,如何与前者进行协调和互动,并共同发挥好空防职能,是一个值得挖掘的问题。在二者的关系问题上,可以借助刑事政策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关系进行类比,如罗克辛教授便说到:“法律上的限制和合乎刑事政策的目的,这二者之间不应该相互冲突,而应该结合到一起,也就是说法治国和社会福利国之间其实也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对立性,反而应当辩证统一起来。”[2]回到空防公共政策与国家制定法层面,二者的合作与交融也应是该种关系状态。“作为人类理性化的创造,法律的存在总是为了因应人类社会生活的某些需要;人类并不是毫无理由地创造了那些行为规则,每一种法律都有其所应担当的社会任务。”[3]国家制定法如是,空防公共政策亦如是,当两种规范形式被放置于同一任务目标和实践环境面前,他们便会殊途同归,并围绕违法犯罪防控这一总体目标来发挥其规范功能。当然,由于规范形式的表现方式不同,空防公共政策虽然与国家制定法具备机能上的一致性,但在实现路径上却有着自己的特色,而这也就决定了空防公共政策在角色定位上的个性内容。
一、空防公共政策的治理优势
哈贝马斯将法律当作一种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社会媒介,能够更加直接地反映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政策,恰好缓解了制定法与社会开放之间的张力,回应了开放社会对于弹性治理的需求:“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这种来回折腾,使得政治理论和法律理论目前处于彼此几乎无话可说的境地。规范主义的思路始终有脱离社会现实的危险,而客观主义的思路则淡忘了所有规范的方面。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紧张关系,可以被理解为对我们的一种提醒:不要固执于一个学科的眼光,而要持开放的态度,不同的方法论立场(参与者和观察者),不同的理论目标(意义诠释、概念分析和描述、经验说明),不同的角色视域(法官、政治家、立法者、当事人和公民),以及不同的语用研究态度(诠释学的、批判的、分析的等),对这些都要持开放的态度。”[4] “实践表明,公域之治的利益表达和实现机制,既需要政治的,也需要非政治的;既需要国家的,也需要社会的;既需要中央的,也需要地方的;既需要反映共性,也需要体现个体差异;既需要实体的,也需要程序方面的;等等。”[5]空防公共政策所代表的规范内容虽然没有传统形式主义、实证主义意义上的法律拘束效力,但是在事实上发挥着与传统意义上的法律相同的功能,即行动者自愿地、普遍地遵守和信奉这些规范,并将它们视为塑造其行为的依据。政策可以确立和提高行动者对其行为安排的预期,可以对行动者提出概要的、大致的政治、道德或者技术要求,可以协调行动者之间的互动;等等。[6]具体说来,空防公共政策在空防安全管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一种弹性治理机制,这种弹性表现在:
第一,空防公共政策的适应性更强。在一般性的假设中,我们会认为,法所具有的普遍性特征决定了“从表层上看,在一定的国家或区域范围内,法应该是普遍有效的,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从深层看,被普遍遵守的法律还应具有被普遍尊重的根据。它要么是具有某些普适的道德性,从而获得了被尊重的内在根据;要么是与一定的公共权力相联系,分享着权力的神圣性。”[7]而立法者在制定规则之初,其内心所期待的普遍适用效果也是在充分了解社会生活的需要后,通过制定一个能够适应于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的尽可能完备、详尽、明确的法律规范来予以实现的。为了达致这一愿景,所有的规则在设计的过程中往往都有意识的预留了许多弹性空间,如《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中的“等”、“情节严重”等立法语言,即是基于兼顾立法的确定性与灵活性所做的设计。但现实是,“任何一个人的天分都没有高到使他具有预见到一切人类将遭遇到的并制定出恰当规则予以调整的先见之明。”[8]国家制定法骨子里的稳定性、有限性、滞后性以及不周延性等特征决定了其在应对纷繁复杂、日新月异的空防安全管理问题时,始终无法回避可能存在的无所适从——法律失灵的尴尬局面。因此,当规则在按照国家制定法所预设的三段论逻辑具体适用于某一事实时,我们或会发现规则的不足;或会发现规则的缺失;当然,也会发现规则的完美适用。诚如周少华教授所言:“作为人造之物的法律根本上无法以其稳定的结构和一致的运作方式满足不断展开着的社会生活的需要,在法律的一般性与社会生活的具体性之间永远存在一道鸿沟,法律的确定性要求与个案结果的具体妥当性要求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立法者虽然会利用各种立法手段尽可能避免这种冲突,但是他却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冲突。”[9]我们认为,现代社会大量日常性、专业性的公共问题,不可能都通过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法规或司法机关的裁定来解决,更多的需要行政机关各个专业性的职能部门、相关的专业人员共同进行快速、有效的决策,并经过法定程序形成公共政策,才能更有效的得到解决。[10]而空防公共政策系由对口的权威部门所做的专业指导,并基于自身的灵活性、不断变动性和适应性,对空防安全管理实践的需要做出快速而及时的反应,这将有助于克服国家制定法缺陷、补强国家制定法功能,更好地满足空防工作需求。
第二,空防公共政策的调整方式更为灵活。治理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来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的增进公共利益。[11]在进行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国家制定法的调整方式基本被限定为命令——强制式,此时国家和公民之间不是合作关系,而是一种暗含对立风险的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这显然并不利于实现社会善治的目标,因为善治意味着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应同时囊括透明、参与、法治、回应、效率、包容、公平、信任、和谐以及安全共十大要素。[12]而国家制定法并不能有效对应包括参与、回应、效率、信任、和谐等善治要素。相反,公共政策以及其所内含的治理方式则能够更好的回应和适应善治的要求,因为公共政策并非建立在等级制或单向传达基础上的规范形式,其对社会生活的调整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愿和自律,设定的行为方式也多为非强制性的,当然,必须承认,公共政策主要依靠社会公权力或者依赖国家权威,依靠来自国家制定法的、国家强制力的某种暗示或者影响来实现其政策目标,故而会在相当程度上对国家制定法的外在约束力产生某种依赖,但这却并非公共政策进行社会调整的主要力量,其更多依赖的还是诸如社会舆论、内部监督、激励机制或其他利益诱导力量来完成空防安全管理的目标任务。
第三,空防公共政策的实现机制更为多样。公法对公权力的控制和规范主要是通过三个途径予以实现:其一,通过组织法来控制公权力的权源,规定不同形式公权力组织的职权和职权范围,并通过分权来保证权力的分立和平衡,使公权力发挥其正面的功能;其二,通过程序法来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方式,设定各种权力运作的方式保证公权力运作符合公平、正义、公开的法治原则,防止公权力滥用损害个人权利;其三,通过对公权力的监督、设定责任、提供侵权救济等方式来制约公权力的滥用。[13]总而言之,这些实现机制都是立足于保障性的国家权力的。而政策的实现机制则有所不同,一方面政策并不排斥各类强制性的实现机制,另一方面,政策又拥有自身独特的实现机制,如通过描述立法背景,宣示立场,确立指导思想,规定目标,明确方针、路线,确认原则,规定配套措施等方式,正面要求相关主体为或者不为某种行为;抑或是通过为其提供行为导向的方式来施加影响,促使其做出有利于公共目标实现的行为选择。[14]
二、空防公共政策的治理模式
空防公共政策因其形式的多样性(涉及决定、通知、批复、意见和函等)、内容的指导性(一般不涉及具体的惩罚措施等量化规范)以及效力的不完整性(在行业内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但却不直接通过司法程序来惩治行为即不直接依靠法定的国家强制力进行约束)等特性决定了其虽然与国家制定法具备相同的功能定位,但在实现治理目标方面,却有着不同的治理模式:
第一,空防公共政策是一种导向机制。空防公共政策通过对控制和预防危害空防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施以指示和引导来发挥其导向机制。
就“指示”而言,正如刑事政策学者梁根林教授所言,“惟有统一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对如何合理而有效地组织反犯罪斗争的思想认识,才能形成反犯罪斗争的合力,协调一致地组织对犯罪的斗争。”[15]空防公共政策根据防控危害空防安全行为所形成的规律性认识,在法治准则的基础上,合理有效地确定了防控的战略、方针和方法等,不仅可以明确该一阶段空防工作的目标,指导空防工作的实践,而且可以统一全系统、全行业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从而形成反违法犯罪斗争的整体合力。如在“六严”工作要求中就提出,公安机关要“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主动进攻,敢于出重拳、下重手……”由此也就确定了民航公安机关一段时间以来针对危害空防安全行为从严、从重处置的基本工作思路和思维倾向。
就“引导”而言,空防公共政策不同于法律是对已有违法犯罪行为的暴力回应,而更侧重于为预防、控制该类行为指明大致的方向、途径和模式。具体而言,这种“引导”又表现在确定了预防违法犯罪的战略层面。如针对危及空防安全的违法犯罪案件,“六严”工作要求对机场公安机关就提出了要“依法‘从严、从重、从快’处理,用好用足法律依据,按照法律法规高限惩处,将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作为常态,坚决维护法律严肃性。”从而确立了现阶段行业对待危害空防安全行为侧重于“打”的战略定位,相应的,也就对机场公安警情处置提出了要求,即“对于工作中出现的推诿、不作为或消极作为等情况,要严肃处理有关责任人员”,以杜绝可能出现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惯性思维,纵容违法犯罪行为的滋生。
第二,空防公共政策是一种调配机制。公共政策尤其是违法犯罪防控政策的本质是社会公共权威为防控违法犯罪而对司法、行政资源进行的配置,公共政策的根本是对可调取的司法、行政资源的分配与组合。[16]因此空防公共政策会根据社会形势(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社会治安形势和国际反恐形势等)、政策目标(打击违法犯罪、预防违法犯罪、消灭违法犯罪、治理违法犯罪等不同目标)、行为状况(违法犯罪高发期、非常态的犯罪形势)等诸方面因素而对惩治与预防违法犯罪的方法、手段等各种司法、行政资源进行调整和配置,从而达到政策主体预期的状态和目标。[17]具体而言,这种调配机制又分为内部调整和外部调整两种,内部调整是对司法、行政包括航空公司、机场的物资、人力资源的调整,也即对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借助包括刑罚和非刑罚方法的途径,调取和运用人力、物力、财力、制度等资源防控危害空防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如对民航安检机构,“六严”工作要求就提出,要“严守安检人员资质和业务培训关,对岗位职业最低资格要求不符合的人员坚决不上岗,对在职教育培训不达标的人员坚决不放权,对达不到人员配备标准数量的通道坚决不开放。要严守在用安检设备管理关,坚决不采购没有取得民航安检设备使用许可证的设备,坚决不启用达不到民航安检设备使用验收检测技术标准的民航安检设备,坚决停用达不到民航安检设备定期检测标准的民航安检设备”。此即为了实现政策目标而合理调配和运用人力、物力资源的适例。外部调整则对是社会资源的调整,这种调整主要表现为对可以用于防控违法犯罪的社会资源的调整和配置,如在社会上形成打击危害空防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的共识、养成自觉遵守民航安保法律法规的习惯等等。事实上,我们会发现,近年来,各类媒体对各种机上不文明行为进行了频繁的报道,并对该类行为的性质、危害进行了大量的宣传,由此产生的效果是,社会舆论层面,对从严管控危害空防安全行为具备了共识;个人行为层面,依法、依规乘机也正在发展成为广大旅客的自觉和习惯。
注释:
[1][美] 高道蕴:《中国早期的法治思想》,载 高道蕴 等 主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6页。
[2][德] 克劳斯?罗克辛 著:《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第二版),蔡桂生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
[3]周少华 著:《刑法理性与规范技术——刑法功能的发生机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
[4][德] 哈贝马斯 著:《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9页。
[5]罗豪才、宋功德 著:《软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81页。
[6]László Blutman, in the Trap of a Legal Metaphor: International Soft Law, 59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605 (2010).
[7]葛洪义、陈年冰:《法的普遍性、确定性、合理性辩析——兼论当代中国立法和法理学的使命》,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5期。
[8][美]列纳?翰德:《法官判决时拥有多少理由》,郑好好 译,载《中国律师》2003年第4期。
[9]周少华 著:《刑法之适应性——刑事法治的实践逻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页。
[10]卢坤建:《公共政策释义》,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11]俞可平 著:《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12]何增科:《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和社会善治》,载《学习时报》2013年1月28日,第6版。
[13]吴昕栋:《软法与权力控制——软法在权力控制中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分析》,载 罗豪才 主编:《软法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1页。
[14]罗豪才、宋功德 著:《软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70页。
[15]梁根林 著:《刑事政策:立场与范畴》,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89-90页。
[16]侯宏林 著:《刑事政策的价值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108页。
[17]严励 著:《中国刑事政策的建构理性》,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5页。
(编辑:黄玉冰)
附件: